江枫的静静的白桦林原文?
推窗远眺鳙鱼野味饵,阳光灿烂。江南,又是一个无雪的冬天,没有雪的冬天真是无聊啊。没有花开,没有鸟鸣,只有阴冷的风,带着湖上的潮气,冰冷地闯入人的心怀。
我走回书房鳙鱼野味饵,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油画,那是北国的白桦林啊,白桦林的诗意,都写在冬天。它是我的战友千里迢迢带给我的,他说,看到这些白桦林,你就会想起高高的大兴安岭,想起广袤的呼伦贝尔草原,想起你的达斡尔战友,想起我们一齐高擎红旗,手握钢枪,在漫天大雪里行进的日子。
望着静静的白桦林鳙鱼野味饵,我的心开始悸动,遐思遄飞。将近四十年前的时光,仿佛一下子就穿越回来。那些火红的年代,那些青春年华,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景,都在眼前闪动起来。
那个冬日的早晨,我们分队出去执勤。天刚微微亮,还有隔夜的晨星似隐似现地挂在西边天上。四处都静悄悄的,大地还沉浸在寂静与朦胧中,草原上没有江南那样密集的村庄与市镇,一眼望不到边的牧场,白茫茫地裹着厚重的雾气,空气中飘着酸酸甜甜的味道,让人想到牧人们蒙古包里的奶酪。
“解放军同志,你们好早啊,我家的雄鸡还没叫呢。”我们在执勤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人是巴特尔大叔。他是一位尽职的守林人。他穿着一件“布贡奇德勒”狍皮长袍,戴一顶“密雅玛格勒”狐狸头皮帽子。他家的小木屋已经飘起袅袅炊烟,那灰白的细烟柱,一点一点地融入清冽的寒气中。
“孩子们,进来喝奶茶吧,刚烧开的。滚烫滚烫,又甜又香。”只要分队从他家的门前过,他总要让我们喝他的奶茶,暖暖身子。记得第一次路过他家,他喊我们进去喝奶茶。我说:大叔,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我想婉拒他的好意。他立刻沉下脸来:好啊,你们看不起我巴特尔老汉,看不起我们达斡尔人,那以后也不要来给我打水扫地,不要给我送木炭,以后也不要从我门前过!我被大叔一顿抢白,弄得好尴尬。
巴特尔大叔说完,把食指送进口里吹响了口哨,立刻一条大黄狗跑了过来,它嗷嗷吠叫着,用尾巴不停地蹭主人的腿,然后后爪着地直立起来,把前爪和身子贴上主人的怀里。看得出,巴特尔大叔是要下逐客令了。
这时副班长阿楚鲁站了出来,他说:大叔啊,牙齿也有咬舌头的时候,雄鹰也有迷路的时候,你发那么大火干什么啊?况且,班长没说错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解放军是有纪律的。不过啊,班长他不懂我们达斡尔人的规矩,没给你面子,他就不对。
巴特尔大叔说:对啊,你们指导员说,军民是一家人,一家人怎么能说两家话呢?
阿楚鲁说:大叔你说得对啊。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替班长做主了,我们喝,都喝。
阿楚鲁带头喝了奶茶,我们也都喝了。巴特尔大叔乐了,嘿嘿嘿嘿地笑得像个孩子。他开心地对我们喊:晚上回来的时候,还要来喝我的“拉里”粥啊!
我们分队又要出发了,巴特尔大叔把右手放上前额,向着天上瞭望了一会儿,认真地说:冬妈妈来了,要下雪了。小伙子们,一路要小心呢。
巴特尔大叔没有子女,老伴也早早过世了。他把我们分队的战士们当成了自己的儿子,和战士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不仅是个守林人,还是一位好猎手。大到黄羊、野鹿,小到山狸、野兔,只要撞上他的枪口,就跑不脱他的掌心。每当有了收获,他总要让我们尝尝他的手艺。
他是位可敬的老人,直爽到你能看清他肚子里有几根肠子。他对军队的爱,不在脸上,在心里。有一次,他等到半夜,还没有听到我们回营的脚步声,怕我们在风雪里迷路,就提了盏红色的马灯,一个人闯入深深的白桦林。遇到我们的时候,他已经冻得张不开嘴。
他一辈子都驻守在白桦林,义务看护这草原上各种精灵出没的仙境,不拿公家一分钱。
走过巴特尔大叔的小木屋,我们就进入了白桦林。
晨光初照,白桦林亮了起来。清晨像是一曲欢快的歌,唱响在我们的心里。沙沙的脚步声像是轻盈的弦乐,伴随我们在林间小径中穿行。在冬日的清晨,在生命的清晨,我们走进静静的白桦林。或许没有人知道,在那遥远的北国有一队朝气蓬勃,充满信心的年轻士兵,正以自己的忠诚,在严寒中,护卫着祖国母亲的安宁。奉献是一种精神,用青春年华奉献的热忱,可以烧开所有自私的阴霾。
我们静静地在林中行进,林中的一切都屏息在冷凝之中,高高的白桦树在晨风里轻轻摇动着枝杈,算是对巡逻兵的欢迎。林间的溪流已经被冻僵了,她的柔波却在冰封下悄悄流动,那潺潺的轻唱,仿佛是送给白桦林的恋歌。
如果说松树是北国英姿挺拔的壮汉,白桦树就是婀娜妩媚的少女。走在白桦林中,你会体验一种神奇,一种神秘,一株株洁白挺立的白桦树,在劲风里摇曳颤动,像是劲歌狂舞,仿佛“萨满”附身,仿佛篝火前的“路日给勒”,酣畅淋漓;而在微风下的轻轻摇动,却宛若少女间的窃窃私语,宛若细语悠长的“乌钦”,讲诉着、吟唱着冰雪里的古老童话、美丽故事。
巴特尔大叔说,小时候他听“斡卓尔雅达干(巫师)说过,白桦林是“腾格日巴尔肯”(老天爷)的三公主白云的化身。老天爷做了个泥人,让他和美丽的梅花鹿成亲,繁衍了人类,而人类聪明起来了,却不再祭祀和供奉天神,还不断地攻城略地,互相战争。老天爷一怒之下,打开天上的水闸,要用暴雨和洪水淹没人类。白云公主不忍人类在残酷的挣扎中毁灭,请求父王收回成命。老天爷根本听不进女儿的苦苦哀求,更加变本加厉。白云公主眼见说不动父亲,而洪水中的人类大多奄奄一息。于是,她不顾一切地偷了父亲的宝盒,向大地扔下一块水晶,变成高高的兴安岭,让人类栖息,又撒下一层黄砂,一层黑土,压下了滔滔洪水。
人类得救了。老天爷却震怒了。他派出天兵天将要将白云公主捉拿。公主下凡逃到了人间,她认为自己没有过错,她愿意一辈子在下界,为老百姓造福,再也不回天庭。于是,老天爷降下七天七夜暴雪,以示对女儿背叛的严惩。白云公主被冻死了,她的身躯和一身白衣白裙,变成洁白如玉的白桦树,千百年来的繁衍,白桦树变成了如今的白桦林。白桦树是达斡尔人的恩人。
妩媚俏丽的白桦树,是大兴安岭的土著,也是呼伦贝尔草原最早的居民。她在2800万年前,就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白桦树是一个多产而又顽强的母亲,她小小的种子,可以随风吹到一公里以外的地方落地生根。只要有一颗种子发芽,日后就会繁衍成林。当她的树干被砍伐后,很快就能从树桩中萌生出新枝干。当一片森林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在废墟中最先出土成林的便是白桦树。
亭亭玉立的白桦树,看似少女般弱不禁风,却有着无比坚毅倔強的性格。就算里边朽死了,依然不歪不倒,树脂莹白,树表光滑。就像我们这些守卫在北国雪原上的哨兵一样,风雨不低头,冻死迎风站。
白桦树的全身都是宝。达斡尔老乡,喜欢用白桦树皮做船、盖窝棚。白桦树皮轻柔光滑,密不透水,巴特尔大叔说,他家的鞋子、帽子、雨伞、水桶都是白桦树皮做成的。对于我们穿行其间的战士来说,最喜爱的莫过于白桦树汁。夏天,热了、渴了,只要用匕首轻轻一划,就有丰沛、甘甜的树汁流出,天然纯净、营养丰富,喝上一杯清爽、甘甜,胜过乳汁。
四十年前,边疆物资匮乏,一张光洁的机制信笺也是奢侈品。战友们就把层次清晰的桦树皮层层剥开,制成“桦树纸”。用它给千里之外的亲人、情人、朋友写信,现在想来,那用桦树皮写的一封封充满激情和白桦树气息的信,该是多么风趣、雅致和浪漫啊。
巴特尔大叔说,白桦树是有军功的树。抗日战争年代,抗联的勇士们,就常常用白桦树皮写信、传递情报。用白桦树皮做的.雪橇,运送物资。白桦树皮还是抗联战士们随时用来行军打仗的鞋子。
我想,白桦树皮如此洁白柔韧,如果现在能把这寒带的精灵做成精美别致的工艺品,投放到温暖的南方去,一定大受欢迎,该会别有一番情趣。
我们的分队,继续在白桦林中前进。时近晌午,有一道白色的弧光从我们面前一闪而过。是谁喊来起来:兔子,是一只雪兔!敏捷的阿楚鲁像一只草原上的猎狗,早已扑了出去,他摘下肩上的“讷莫”短弓,顺手朝着白光就是一箭。随后,他冲了过去,笑嘻嘻地提着一只大耳朵白兔的肥硕的后腿,开心地叫了起来:晚上回去打牙祭了!
副班长阿楚鲁,参军前是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好猎手。是达斡尔人“苏木哈日布贝”上的常客,不管是骑马射还是立地射,他都百发百中,每次射箭比赛,都能得到“莫尔根”(好箭手)的称号。阿楚鲁说,射箭比赛在达斡尔人看来,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每次赛前,都要杀一头肥猪给射手们享用。
生性爽快的阿楚鲁也有羞涩的时候,他有一个姐姐叫娜仁花,他说姐姐的汉族名字叫月亮。他说姐姐是家乡最漂亮的姑娘。说到姐姐他的眼睛都会闪动骄傲的光芒。战友们就逗他:阿楚鲁啊,把姐姐嫁给我吧?我愿意娶你的姐姐做新娘。每当这时候,阿楚鲁就会像小姑娘一样羞红了脸:不行啊,不行啊,我们达斡尔的姑娘是不嫁给外族人的。我们就又逗他说,那我们在南方给你找个姑娘,你要不?阿楚鲁就乐了,大声嚷着:好啊,好啊,不过要像姐姐一样漂亮。于是,大家就一起哈哈大笑。巡逻的疲惫一扫而光。
也不知为什么,在严冬里巡逻,只要听到阿楚鲁的歌声,我就想喝酒,痴迷那种酒入热肠的感受。只要想到,我就会拿出行军壶,咕嘟嘟喝下一大口白酒,那种仿佛滚烫的开水,带着热流翻腾着从喉咙直下丹田的感觉真爽。大家都来一口啊,驱驱寒气。我开心地喊着,行军壶在战友们手中传递,这种干喝只有老战士才吃得消。新战士们有的涨红了脸,有的被呛得使劲咳嗽。于是,我们就在笑声里,继续在林间向前走。
喝过了酒,你就能听到白桦树的歌唱,声音柔和而低沉,那凛冽的寒风也不再觉得刺骨,风声萧萧,像是马头琴优美的旋律。这时候,你再看那些洁白的白桦树,晶莹的树皮里会透出新鲜的红晕。是不是我们这些傻大兵哈出的酒气,把白桦树也熏醉了,还是我们以苦为乐的傻样,让她们——树中的少女羞红了脸?哦,白桦树,不要笑我们的傻像,我们知道脚下的责任,肩上的分量,在风雪里手握钢枪,我们知道自己的背后,是祖国母亲的万里江山,是亿万和平人民的笑颜。
巡逻累了,我们会在林间的空地上,围坐休息。大家总会喊能歌善舞的阿楚鲁来一个。阿楚鲁是从不知道推辞的,好像只有他可以当仁不让。阿楚鲁最喜欢唱“扎恩达乐”——达斡尔人的山歌。唱什么呢?他问。《农夫打兔》。大家一起喊。《农夫打兔》唱的是一个笨农夫和聪明兔子的故事。农夫不但没有打到兔子,还丢了柴火,断了打兔子的耙子。这个故事诙谐幽默,加上阿楚鲁挤眉弄眼的演唱,总能把大家逗得开怀大笑。空闲的时候,阿楚鲁还会教大家跳“路日给乐”,这是一种无伴奏的舞蹈,大兵们就用喊歌来伴舞。我们最喜欢喊的是“哈莫——”这是达斡尔人嘴里黑熊的吼声。
阿楚鲁不愧是达斡尔人的好猎手,一路上,他竟然用他的“讷莫”,射中两只猞猁、一只兔子,还砸开冰面,水洼里捉到一只胖头鱼。大家商量,送一只猞猁和胖头鱼给巴特尔大叔,好好酬谢这位热心拥军的老模范。
嘿,我说战友们,你们闻到雪味了吗?走在队伍前头的阿楚鲁问。没有啊,没有啊,雪有什么味啊?大家疑惑地问。
阿楚鲁走到一棵挺拔修长的白桦树前,用鼻子使劲地闻了闻,自言自语地说:要下雪啦,要下雪啦。白桦树告诉我,暴风雪就要来了。
大家还在狐疑,仰头看看天空,可不是吗?白桦林的树梢上,已经稀稀疏疏地飘下了雪花。雪花在林间飞舞,像是千万只晶莹剔透的水晶蝴蝶。我们大家立刻都闻到了雪的滋味,那是白桦林里独有的芬芳。这芬芳的香气,像是苹果的香、水蜜桃的香,像是橙子的香,又像是荔枝的香……我们分队的每个战士都闻出了那芬芳的雪味,那是我们各自家乡的味道啊,为了家乡的和平安宁,为了家乡的草更绿,花更红,为了白兰鸽能在蓝天下自由地飞翔,我们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静静的白桦林,走在苦寒的巡逻路上。
雪开始在白桦林里飘落。先是一朵一朵的雪花,像是我江南家乡春天飞扬的柳絮,悄悄地飘,轻轻地落。然后,起风了,雪也就越下越大。一阵大似一阵的风,把雪吹得纷纷扬扬,撕扯成团团片片,顷刻间,天地就浑然一色,弥漫的风雪,把白桦林染成了一个无色的世界。
呛着风,顶着雪,我们继续沿着小径巡逻。“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一不怕死,二不怕苦。”喊着这样的口号,我们歌声嘹亮,步伐坚定。在这样的冰雪世界里,仿佛整个世界,都没有了色彩。没有红花,没有绿叶,唯有白色的白桦林和银白的天空,银白的大地。或许这就是天地间的本色,或许这就是我们军人坦荡胸怀冰清玉洁的本色。在这空茫苍凉的银白世界里,我们与天地一色,肝胆具澄澈。
傍晚,在回来的路上,一直不曾吭声的老张,悄悄地对我说:班长,这个春节能让我回家探亲吗?我知道战备任务忙,一直没好意思对你说。我爱人给我来信,说她就要生孩子了。老张是个服役五年的老兵,他的家在千里之遥的南国岭南。他已经有四个春节,留在兵营、走在巡逻线上。今年春天他爱人来队探亲,真巧就有了身孕。我对他说:好的,我一定向连部反映,让你回家过个三口人的团圆年。老张听了,紧紧握了下我的手,然后摘下自己的行军壶,两眼放光地说:班长,喝口我的酒,西凤酒,我带在身上好些年了,从来都没喝一口。我被这老兵的真诚感动了,说:留着回家喝吧,别可惜了这样好的酒。
副班长阿楚鲁偷听到了我和老张的对话,把肩上扛着的猞猁和兔子,塞到老张怀里:大着嗓门乐呵呵地说:这个野味,你们岭南一定没有,你带回去,给咱们嫂子补身子。战友们听到老张要生孩子了,一起围拢来向他祝贺。有那调皮的家伙就喊上了:老张啊,真有你的,那么几天就让嫂子怀上了兵崽子。长大了,你可别忘了让他也来咱这白桦林巡逻啊。
午夜,雪住了。我们看到在容易迷路的地方,挂着一盏橘黄色的马灯。那是巴特尔大叔的马灯。我们知道,巴特尔大叔还没睡,他还在等着听巡逻分队的脚步声。
将近四十年过去了,我的生命之舟正驶向耳顺之年,霜雪已经悄悄地染上两鬓。多少事,多少人随着历史年轮的滚动,都淡忘了。但是,我却永难忘怀,年轻时走过的那洁白胜雪的白桦林,和那路上的人,一起行走的人。
哦,冬日的白桦林,静静的白桦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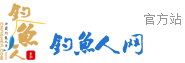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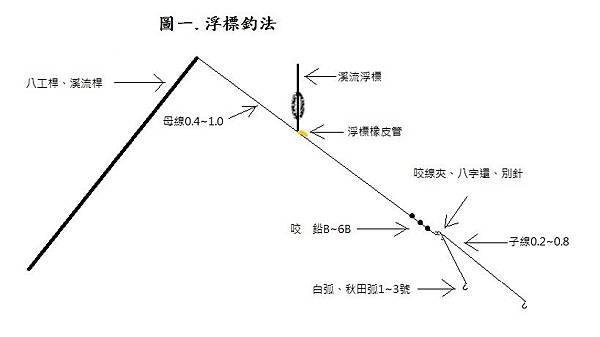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