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的,下乡头侬晓得,没好好的路,都是污泥,一塌糊涂。侬看看此里,勿要太清爽,穿一身西装笔挺来钓鱼都是可以的。侬勿要笑,真是可以的。呵哼。”老唐起了兴致,清了清喉咙里的痰。
他呷一口保暖瓶里的茶,拧上瓶盖继续讲,“再过一阵子,油菜花开的辰光,阿拉老早都要去钓老板鲫鱼,这是顶好的辰光。称为老板就是大鲫鱼,这种四两的阿拉叫伊麻将牌,老板嘛顶起码要一斤多一点。侬拎去菜场卖,比一斤的甲鱼还要贵。大点的鲫鱼红烧烧,塞点肉。”老唐讲到这里,老张忍不住回头笑了,那是酒逢知己的味道,“再弄点竹笋,噢唷,勿要闲话来。”
老唐换了一个站姿,眼睛望着池塘里,继续讲,“老早侬也晓得的,都是野浜。阿拉这段辰光不会错过的。菜花开,清明前,就是钓老板的辰光。鱼经过一个冷天下来,肉也壮,而且肚皮里杀开来都是鱼籽。跟侬讲,河鲫鱼是雌的多,雄的少,十条里面八条雌……”
话到一半,老唐停住了。原来是水里的浮标动了,那种并不十分明显的动静外行是看不出来的,记者不明就里,继而观察老唐,他的眼睛此刻紧盯着水面的鱼线和竿子,那简直就是小朋友见到别人在玩玩具的表情。他喃喃讲,“笃定,笃定……诶,遛遛白相相。”再转过来跟记者讲,“钓鱼呢,就是这个感觉。”
老张拱起鱼竿将鱼拖到岸边,鱼在水面划出一道“V”字形的浪花,老唐已经认出了水里的家伙,“这条叫三条金,档次比河鲫鱼要推板(差)一点,你看鱼鳞片的颜色和河鲫鱼不一样。不过伊这条小了,这种阿拉叫毛毛雨。”
三条金被打捞起来,我们凑近一看,果然背上有三道金色的鳞片,只是鳞片看起来不太自然,样子怪难看的。老张说,这种鱼只有鱼塘里有,是人工杂交出来的品种,野浜里是没有的。
我们边上站了不到半个钟头,老张已经钓上了两条鱼,这也是鱼塘里通常的上鱼速度,因为是人工放养的,鱼群的密度其实远比野浜要高,所以但凡像老张这样熟练的钓客出手,一个下午钓十来斤是没有大问题的。而这种收费的鱼塘也有规定,凡是钓上钩的鱼绝不能放回水里去,上一条就算一条价钱。钓客多的时候,鱼塘边都会有好几个看塘的人手盯着。不过这天因为下雨又无客人,看塘的人便猫到边上的小木屋里去了。
“赤佬大概去困中午觉了。”老唐看了一眼对面的小屋,然后继续讲他自己的钓鱼经,“钓鱼关键是遛鱼要看水平,有种水平推板的,遛了老多辰光,结果"剥脱"一记,鱼没了。有种人遛不了多少辰光,诶,鱼照样上来了。钓鱼里厢的窍槛多了,比方讲下塘子(下鱼饵),看风向,还有温度,都是交关要紧。”
“风向有什么讲究?”记者问。
“东面吹来风就要坐在西面,要坐对风面,水面还要吃得到一点风头,这样水里会有一点浪头,有浪头空气就好,钓鱼和空气好不好大有关系来。鱼要是空气不好,闷了,就要浮起来透气,再闷就要翻肚皮了。侬看到对面水里有一只泵嘛?热天的时候就要开的。”
“浮起来不是应该更好钓吗?”记者问。
“诶,先生,我看侬是真的一点都勿懂啦……鲫鱼呢,就是沉在下头的,吃食就是在底里吃的。鱼吃食不是靠牙齿去咬,是用吸力的。”老唐抬起肘,捏着手中正在燃着的香烟打比方,“香烟是食,鱼呢就嘴巴一张”他用另一手攒成一个鱼嘴,"啵"一记吸进去,浮子起来侬一拎就钩牢了。但是鱼吸进去,伊吐起来也快的,"啵"一记也就吐特了。有种朋友就问,哪能老是钓不着的,不懂的朋友永远搞不清爽。”
老唐讲起来绘声绘色,老张也听得哈哈直笑,笑到手里竿子也晃起来了。
“侬为啥欢喜钓鱼呢?”
“啊?”
“为啥欢喜钓鱼呢?”老唐毕竟上了年岁,听力有所不济,好多问题都得重复多遍去问他。
“钓鱼顶刺激的辰光,就是搭到大鱼。遛鱼的辰光,又是欢喜,又是紧张。下头"哐啷哐啷"在摒,上头心跳一百多跳。抄网一抄,鱼就到手了,就是开心啊。有辰光摒了半天,"吧嗒",(水里)力道哪能没了?噢唷,鱼逃特了,就是晦气呀。”老唐嘴里的拟声词最多,惟妙惟肖。
“又来了,侬看。”老唐手一指,老张手里又上鱼了,岸边一直在听讲话的老张眼睛可还是盯着水面。老张站了起来,和水里的鱼儿联手将竿子拱成了一轮星月—准备收鱼了。
“白相相,白相相,笃定。”老唐一面对老张说,一面还在观察,他的意思是让老张慢一点,多遛一会儿。
老唐讲,遛鱼最有意思是一个“扳”字,就是和大鱼较劲,他欢喜大浜,活水浜,因为流水里的鱼同样十斤重,力气和鱼塘里的完全是两码事—“钓大鱼是交关刺激,老早阿拉去外地,到常熟去,那里有只野浜比青浦的浜要大多了,一车子开过去40、50个人,跑到湖浜进去大家就散开了,自己寻自己的位置,侬坐了此里,周围就看不到人了,侬讲讲这个浜有多大。这个里厢扁鱼都要三斤一条,碰到鲤鱼、草鱼十几斤不稀奇的,我扳起来照样是笃笃定定的。”
讲起钓大鱼的往事,老唐一双底色偏黄的眼睛就像干柴遇到火,轰一下亮了起来。老唐不知道,此刻的他和《老人与海》里的那个桑蒂亚戈像极了。
男同志有这个爱好,老太婆还要提意见?
老唐拧开水瓶喝水,岸边谈话也有了一个间隙,这时候反而听见了林子外头外环线上隆隆的车流声,如果不知道情况,那种有着共鸣的动静听起来像是火车经过一样。
不知什么时候起有了些风,藻绿色的水面有了涟漪。刚才对岸又来了一个钓客,忙活了一阵,现在也已经坐定如渔翁了。
话说一会儿功夫,老张又一条鱼上钩了,大概是因为热闹的缘故,老张一直站到现在,他照例用抄网收起鱼,眼睛尖的老唐又看出问题了—“这条鱼哪能眼睛爆出来呢?眼睛出血了,啧……老板不在呀现在,要伊伐啦?”
老张和老唐想到了一起去,他把鱼脱钩后悄悄往钓台边的夹缝里一滑,鱼又滑进水里了。“赞”,老唐说。“是有点吓人到怪。”老张回头讲。“今天钓的这些鱼一般回去怎么处理呢?”记者问老张。“自己吃咯,要么就送人。”老张答。“阿拉钓鱼的人呢其实是不欢喜吃鱼的,多吃有啥吃头。”老唐补充。“家里人对你们钓鱼怎么看?”记者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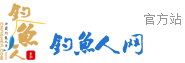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