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无聊的时候就更加容易恋物。
这些天我很无聊,有一天甚至无聊到从天桥一直溜达到积水潭的程度,看看地图你就知道有多远。
这些天我就琢磨着淘汰我那个28―200的狗头,换个比如28―80再加个80―200什么的。
我还琢磨着是不是该玩玩反转片了吧,什么又是正片尼?反转片和正片是不是一种东西的两个马甲尼?我不知道我得打听打听先。
我还在琢磨着,要不要买件Gore-tex材料的冲锋衣尼,或者,搞两条两截儿的速干裤吧,速干裤是Columbia的好泥还是Seatosummit的好尼,奥索卡什么时候能打个2、3折尼,秀水的Gore-Tex是真的还是假的尼,我需不需要一顶Cool-Max的帽子尼?
我还想啊,我的破Nikko背包要不要升级成BigPack尼。要不要,买一双Vibram底的徒步鞋尼。
北脸咋就那么贵尼。
玩反转片是不是还要买个观片器尼,用放大镜将就着看行不行尼,要不要买个底扫尼。旧货市场会不会有便宜的幻灯机尼。
我的军用指北针是不是不太准尼。可乐瓶子和Laken水壶差别有多大尼,Laken和Sigg有多大差别尼。蛋托的防潮垫比搓板的怎么样尼。Leki那款能当独脚架使的雪杖好不好用尼。
直到我坐在三夫国贸店旁边的肯德基喝着一杯巨可的时候,我还在不停地琢磨着,想啊,想啊。
我想起了在秭归的杏花村招待所门口,Paul他们第一眼看见我的时候。同学们根据斜插在我背包后面的那根烂登山杖,错误地判断出,徒步这活儿我是很有经验地。Kao,天知道,那是我在武昌等车的二十分钟里,为了自我营造一下徒步气氛,鬼使神差地花300两银子买的,想起来我就心疼。当时我还怯生生地问那个mm,这个,这个是,登山杖吗是吗?
在登山杖之前,我最专业的装备是一双Gore-Tex的Coleman登山鞋,当然买之前我并不知道它是很专业地,我只知道三夫卖865百盛也卖865而新街口只卖606地。
在Coleman鞋之前,我最专业的装备是一个Saxo两用头灯,那可是一个好东东,营造气氛要比手电筒效果好得多地。
我想起了我的价值35块钱的哨子,它吹起来还没有Paul那个2块5的响亮,就是体育老师用的那种。
我想起了Fenfen先是穿着旅游鞋,后来穿着在新培石买的低帮解放鞋永远飕、飕、飕地走在最前面把我甩下2、300米。我想起在沙砖场过一条小河沟的时候,我笑她每次踩进水里的都是她的脚,话音刚落我就在岸边扑通一声,在我的膝盖上留下了烙印。
我想起了在重庆穿着肮脏的牛仔裤逛大都会时的快乐,我想起了在布达拉宫看mm们边爬楼梯,边抱着氧气袋鼻子里插着导管吸氧的快乐。我想起了那支奇形怪状的队伍,Paul穿着透明雨衣,阿峰套着自行车雨披,小L穿着MHW冲锋衣,Fenfen缠着一身乱七八糟的塑料布,我想起了我戴着草帽,和他们一起走在春天的风箱峡时的快乐。
我想起了Paul用他那架破、破、破Pentax拍反转片,用他的“旁轴”傻瓜拍负片,而我的F90X频频死机时的快乐。我想起了莺莺,她以为我用Nikon我的摄影技术就会高那么一点点,而我暗笑,其实我只会用全自动模式时的快乐。
我想起了,我想起了在念青唐古拉以北的天堂,我的防风打火机怎么也打不着的快乐。那个快乐的藏族老兄从棉袍里掏出一盒平凡而渺小的火柴,嗤――,着了。
我想起了我买的第一个帐篷,那顶一下雨就漏的探路者带给我的快乐。
业余着是多么的快乐啊。
而此刻,我却坐在这里盘算着,盘算着喝完这杯可乐之后,将要属于我的装备们。
盘算着将要不再属于我的钞票们……
这可是,一大笔钱啊。而我不过是想去爬爬古北口,想去木兰围场骑骑马,想回长白山区寻找寻找从前地影子。
……
不!
STOP!!!
不,我要继续业余下去!
业余着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快乐啊,我不要失去这些快乐,我不要失去这些业余而简陋的快乐。
在回家的地铁上我琢磨着,我要用省下的这笔钱的零头,给自己买一个信封式的抓绒睡袋,在下一次旅途中我将美好地躺在里面幻想着,幻想着我的永远买不起的后海四合院,幻想着六缸、五档、四驱的手排Cherokee,三枪的数字投影仪,两个老婆一起过的后半辈子。
我要继续业余下去,我要永远业余着并快乐着,在业余中快乐着,在快乐中业余着,永远因为业余而快乐着,因为快乐而业余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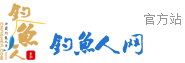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