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偏爱重步兵 翻译自《Alpinist》Vol.16,Mountain Profile,The Matterhorn 文/Herve Barmasse、Luca Maspe
南壁上的新纪元
当“茨姆特之鼻”吸引了全欧洲最优秀的登山家时,南壁上似乎已没有继续开拓的可能。然而只要细心观察,还是能够发现一些新颖,并具有相当难度的路线。就拿加布来说,他就设想能在南壁上岩石构造最紧凑的区域开辟一条体现出现代攀登风格的路线。2002年8月15-16日,他和拉瓦切托完成了南壁Pic Muzio上最苛刻的一条路线:Padre Pio Pray for Us(皮奥神父为我们祈祷),位于科尼兹路线和花儿刃脊中间。2004年3月,两名来自瓦莱达奥斯塔的年青攀登者――马西莫•法里纳(Massimo Farina)和赫维•巴玛塞(Herve Barmasse,本文作者之一)――完成了这条路线的冬季首攀。
在当时,年青人中向我这样依然关注马特洪峰的人并不多。更早之前,23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在马特洪峰上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条路线:2000年8月14日,我和布里耶的年青向导帕特里克•波莱托(Patrick Poletto)首攀了南壁“德•阿米西斯”路线和“卡萨洛托-格拉西”路线之间的陡壁,难度6a+max。两年后,我率先以solo的方式完成“卡萨洛托-格拉西”路线,而当年正是我父亲完成了这条路线的冬季首攀。
出发时气温很低,向上能看到峰顶的十字架在阳光下闪烁。踩在积雪上发出的脚步声惊动了岩羚羊,但循着清晨的微风依稀可以闻到它们身上的气味。我顺着通向迪法耶山脊的沟壑迅速上攀,然后向右切到我和帕特里克在2000年攀登过的岩石路段。那次回来后,我曾感觉马特洪峰已然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现在我能感受到的只有孤独,乌云遮蔽了顶峰,开始下起雨夹雪。我并不了解这条路线,但我很清楚首登者的传奇故事。即使只是在脑子里想一下雷纳托•卡萨洛托和贾卡罗•格拉西的大名――当然也包括所有先于我攀上这面岩壁的前辈,就足够让人肃然起敬了。
小心起见,我在前三段绳距固定了路绳。然后一块落石砸中了我的头盔,警告我南壁究竟有多危险。我觉得快速通过或许是明智的决定。
我边攀登边幻想,要是马特洪峰是由坚硬的花岗岩而不是松动的石灰岩构成该会怎样?但我很快就提醒自己,这不够理想的岩石构成正是诸多使得马特洪峰与众不同的原因之一。这里的每一步前进都需要理智,攀登非常艰辛并且要时刻警醒。我用了至少四个小时才通过最后一段被粉雪覆盖的精巧的绳距,到达丁达尔峰附近。眼见暴风雪正从西方逼近,我决定去“Carrel”木屋。夜里我梦见了啤酒和巧克力,以及在过去150年的攀登历史中,马特洪峰在攀登者心中呈现出的不同形象。
未来
马特洪峰的攀登历史见证了登山运动自身的发展。自传奇性的首登后,每个时期最牛逼的攀登者都为我们奉献上了一幕幕经典。今天,两条传统路线已经沦落为拥挤的观光胜地,路绳差不多从山脚一直固定到顶峰,并且居住在山峰两侧山谷中的当地向导也为了利益分配的问题争执不休。从今往后,或许只有关于探索新路线以及对旧有路线重新诠释的想象才能给我们足够的理由去重新讨论大鸟嘴(译注:就是马特洪峰)。
图:1994年3月13日,凯瑟琳•黛斯特薇尔和埃里克•迪坎普(Erik Decamp)分别solo博纳蒂路线和施密德路线,然后在顶峰回合。 photo/Pascal Tournaire
未来几年内,还有一些路线有待以solo或是冬季攀登的方式重复。首先应被考虑,当然也是相对较简单的,就是用自由攀登的方式重复“茨姆特之鼻”上现有的器械攀登路线。这其中“皮奥拉-斯坦纳”路线可能是最有希望的――就我所知,还从没人尝试自由攀登这条路线。当然这一切需要时间和勇气,毕竟北壁上的环境和岩石状况是无法同那些日照充分的岩壁相提并论的,在那些地方,年青的自由攀登爱好者可以在相对安全的水平上反复检验自己的攀登技能。
时至今日,你很难在八月的阿尔卑斯找到一处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地方。但在马特洪峰,只要避开传统路线,依然有机会体验到这份孤独。那些位于最寒冷、最不友好的岩壁上的路线很难接近,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日渐荒凉,值得你去重新发现它们,赋予其新的生命。
尽管关于马特洪峰现有形象的种种定义最终都难免沦为陈词滥调,但“后现代”攀登期的马特洪峰依然是一座未被人工器械完全驯服的严峻的山峰。即使在我们所处的当下,她依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2003年8月18日,“la Cheminee”――这条狮子山脊上,曾考验过温伯尔和卡雷尔的著名通道――在经历过一个异常炎热的夏季后哄然坍塌。马特洪峰的山体再次发生了变化。她将来会具有何种形象,会被赋予什么样的意义,这一切都无从所知,但作为一名在她的威严下成长的攀登者,我无法想象她会被人们遗忘。
(全文完)
备注:原作者Herve Barmasse和Luca Maspes,按前者第一人称叙述,初稿为意大利语,由Linda Eklund和Christina Svendsen译成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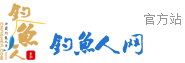







 |
|